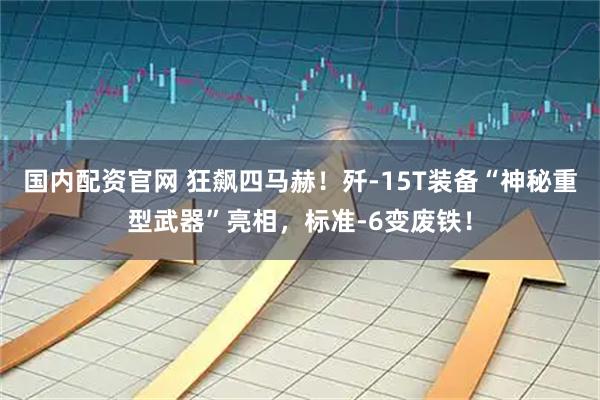1.
除夕夜,窗外鞭炮声震天响,炸得人心慌意乱。
我也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个炮仗,只等着那一根引线烧到头,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炸个粉碎。
七点半,春晚的开场舞正热闹,电视里的主持人笑得满脸褶子,喜气洋洋地说着团圆。
我把最后一双筷子“啪”地一声拍在桌上,力道不大,但在死寂的客厅里,这一声显得格外刺耳。
年夜饭上桌了。
没有热气腾腾的饺子,没有寓意吉祥的红烧鱼,也没有那只我念叨了半个月的土鸡。
暗红色的折叠圆桌正中央,孤零零地摆着一碟黑乎乎的腌咸菜。
那是婆婆从老家带来的,用的是最廉价的芥菜疙瘩,黑得发亮,透着一股陈年的死咸味。除此之外,桌上只有三碗白米饭,连口热汤都没有。
展开剩余91%“吃吧。”我拉开椅子坐下,声音冷得像是从冰柜里捞出来的。
老公陈志刚坐在我对面,他那张常年被风吹日晒弄得粗糙黝黑的脸上,没有任何表情,只有眼角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。
他穿着那件领口已经洗得发白的灰色卫衣,整个人缩在阴影里,像是一尊沉默的石像。
婆婆王桂花坐在侧面,她缩着肩膀,在那件穿了五年的暗红色棉袄里显得更小了。她看看儿子,又看看我,浑浊的眼珠子里满是惊恐。
她那双枯树皮一样的手抓着衣角,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掉的黑泥。
“悦悦……这……”婆婆嗫嚅着,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,手里的筷子举起来又放下,愣是不敢伸向那碟咸菜。
我看着她这副唯唯诺诺的样子,心里不仅没有一丝怜悯,反而升腾起一股报复的快感。
就在三个小时前,陈志刚一瘸一拐地进了家门。我以为他会带回这一年的辛苦钱,带回我们盼了一年的希望。
结果,他避开我的眼神,当着我的面,把他兜里那张还带着体温的银行卡,直接塞到了婆婆手里。
“妈,这五万块钱,您收好。”
那一刻,我正在厨房切姜末,刀锋一偏,差点切掉半个指甲盖。
五万块。
那是他跑了一年长途冷链车,没日没夜熬出来的年终奖。是我们计划着明年翻修老房子的启动资金,是我想要备孕生孩子的底气。
他连个商量都没有,甚至连个钢镚儿都没给我留,全给了他妈。
行啊,陈志刚。既然你要当那感天动地的大孝子,那我就成全你。
我从兜里掏出手机,解开锁屏,点开那张早就准备好的转账截图。
“妈,既然志刚这么孝顺,我也不能落后。”
我把手机屏幕调到最亮,直接怼到了婆婆面前,语气里带着一丝尖锐的嘲讽,“您看清楚了,这是我年底的双薪,加上年终奖,一共三万块。就在刚才,我也全转给我亲妈了。”
婆婆浑身一抖,像是被烫着了一样往后缩。
我没给她躲避的机会,继续笑着说:“我妈说了,她帮我存着,免得我乱花。所以啊,妈,志刚的钱您存着养老,我的钱我妈帮我存着。”
“咱们这个家,现在账上就剩二百块钱。这一碟咸菜,就是咱们二百块钱的年夜饭标准。您别嫌弃,这可是咱们两口子一片孝心换来的。”
我说得理直气壮,字字句句都带着刺,只想扎得他们母子俩鲜血淋漓。
2.
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电视里传出小品演员夸张的笑声,和屋内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形成了荒诞的对比。
我死死盯着陈志刚,等待着他的爆发。
按照他对那个家的维护程度,按照他那死要面子的脾气,这时候他应该拍案而起,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懂事,骂我算计,甚至可能会掀了桌子。
我都想好了,只要他敢掀桌子,我就敢立刻去民政局排队。这日子,我受够了。
可是,陈志刚没有。
他只是低着头,死死盯着那碟咸菜,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。他放在膝盖上的那双手,紧紧攥成了拳头,手背上青筋暴起,指节泛白。
“悦悦……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,像是含着一把沙子,“钱给妈……是有原因的。”
“原因?什么原因?”
我心里的火蹭地一下窜到了天灵盖,猛地站了起来,“陈志刚,结婚五年,这种话我听了多少遍?”
“前年你弟弟盖房,你说长兄如父,借了两万,至今连张借条都没有;去年你表妹出嫁,你说要撑场面,包了八千的大红包。我林悦在你眼里算什么?是这个家的免费保姆,还是跟你搭伙过日子的外人?”
我越说越激动,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。
我是个社区生鲜超市的理货员,每天早上四点就要爬起来去接货。冬天冷库里的温度是零下十八度,我的手常年被冻得红肿,一沾热水就痒得钻心。
为了省几块钱,我从来不舍得买好一点的护手霜,都是趁着超市试用装打折的时候囤几瓶。
我这么抠门,这么算计,是为了谁?还不是为了在这个城市能有个属于我们的小窝?
可他呢?
他常年跑长途,一个月回不来几次。每次回来,不是倒头就睡,就是闷头抽烟。家里的灯泡坏了是我换,马桶堵了是我通,甚至连我都发烧到三十九度,还要自己爬起来烧水吃药。
这些我都能忍。我图他什么?图他老实,图他肯干,图他那种笨拙的踏实感。
可今天这五万块钱,彻底击碎了我最后的防线。
这不是钱的问题,这是信任的问题,是态度的问题。他防我像防贼一样,宁愿把钱给他那个连银行卡密码都记不住的妈,也不愿交给我这个和他同床共枕的老婆。
“吃饭吧。”
陈志刚终于抬起头,他的脸色灰败,眼窝深陷,黑眼圈重得像是被人打了一拳。他避开了我的质问,拿起筷子,颤抖着伸向那碟咸菜。
他的动作很慢,慢得不正常。
当他的手伸到灯光下时,我才发现,那只平日里有力的大手,此刻竟然在不受控制地细微颤抖。手背上布满了细碎的伤口,有的已经结痂,有的还渗着血丝。
就在他的筷子刚要碰到咸菜的一瞬间,手腕一抖,筷子碰到了碟子边缘。
“咔哒”一声轻响。
一块碎瓷片被碰掉了下来。原来那个碟子本来就有个缺口,被他这一碰,彻底裂开了。
陈志刚愣了一下,下意识地伸手去捡那块碎瓷片。
“嘶——”
锋利的瓷片边缘划破了他的手指,鲜红的血珠子瞬间冒了出来,滴落在黑乎乎的咸菜边上。
红色与黑色,在昏暗的灯光下,显得触目惊心。
3.
“志刚!”
婆婆惊呼一声,想要站起来,却又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压住了一样,只欠了欠身子。
陈志刚像是没感觉到疼一样,随便在裤子上抹了一把血,把那块带血的咸菜夹起来,放进嘴里,用力咀嚼着。
“妈,吃饭。悦悦,你也吃。”
他低着头,机械地扒了一口白饭,腮帮子鼓动着,那样子看起来不像是在吃饭,倒像是在吞咽着什么难以下咽的苦药。
我看着那滴落在碟子边的血迹,心里的怒火突然像被泼了一盆冷水,瞬间变成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。
这几天,陈志刚确实有点反常。
他大概是半个月前回来的,比往年都要早。往年跑冷链,越是年底越忙,运费也越高,他通常都要跑到腊月二十九才舍得收车。
可今年,腊月十五他就到家了。
回来那天,他没带任何行李,只背着那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。一进门,他就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,洗了足足一个小时。
出来的时候,他换上了那条宽松的黑色运动裤。
从那天起,我就没见他穿过别的裤子。
而且,无论我什么时候进卧室,他总是已经躺在了被窝里,或者是背对着我在穿衣服。我想亲近他,手刚碰到他的腰,他就像触电一样躲开,说是太累了,腰疼。
我以为那是借口。我以为他在外面有了别的温柔乡,嫌弃我这个整天和死鱼烂虾打交道的黄脸婆了。
甚至前天晚上,半夜两点我醒来,发现身边是空的。
我走到阳台,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地板上,背影佝偻成一团。手里夹着那种五块钱一包的廉价香烟,脚边已经丢了一地的烟头。
冬夜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,他就那样穿着单薄的秋衣,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我想推门出去叫他,却看见他突然弯下腰,双手死死抱住自己的右腿,肩膀剧烈地颤抖着,喉咙里发出一声被压抑到极致的呜咽。
那一刻,我以为那是生活的重压让他崩溃。毕竟今年运费降了,油价涨了,日子不好过。
可现在,看着他那只带血的手,看着他那条即使坐着也显得有些僵硬的右腿,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。
我下意识地看向他的脚踝。
他穿着一双洗得起球的深蓝色棉袜,袜口已经松了,软塌塌地堆在脚踝上。而在那袜口上方,隐约露出一点不正常的青紫色,像是严重淤血后的痕迹。
“你的腿怎么了?”我忍不住问了一句,语气虽然还是硬邦邦的,但声调已经低了下来。
陈志刚扒饭的动作停滞了一秒,随即若无其事地把腿往回收了收,藏在桌子底下。
“没事,老寒腿犯了。冷库里进进出出,冻的。”
发布于:湖北省富华优配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